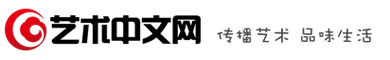|
|
“酸檸檬”能量|共藝聯(lián)盟的“自然時(shí)刻”
“其首先解決的,不是照亮誰,而是為’燈泡’提供能量”。 后疫情時(shí)代的今天,當(dāng)我們再一次將目光聚焦“自然”時(shí),實(shí)際是以怎樣的角度和姿態(tài),在旁觀角度,審視當(dāng)下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生態(tài)?命題有點(diǎn)大,卻是在觀看2023年2月25日于太原千渡長江美術(shù)館開幕的展覽“自然時(shí)刻-新媒體共藝聯(lián)合展”時(shí),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。
“自然時(shí)刻-新媒體共藝聯(lián)合展(以下簡稱“自然時(shí)刻-太原站”)”是藝術(shù)共創(chuàng)聯(lián)盟[nature moment自然時(shí)刻]的一次主題創(chuàng)作展,展覽由藝術(shù)家史健、城市插畫師李丹、空間敘事者nimo、創(chuàng)意策劃師馬唏、攝影師一乙、聲音藝術(shù)家徐斯韡、裝置設(shè)計(jì)師Sting、數(shù)字藝術(shù)設(shè)計(jì)師高宇等不同領(lǐng)域的創(chuàng)作者共同呈現(xiàn)。現(xiàn)場30余件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,通過視覺、文本、數(shù)字科技、聲音、觸感、情境體驗(yàn)等方式,對“自然”這一命題展開定義。有趣的是,看似輕松的展覽敘事,卻始終都在一個(gè)謹(jǐn)慎又略帶沉重的氣氛中,盡可能地用疏松容易的口吻將每件作品化為片段,構(gòu)建關(guān)于“自然”的體會(huì)。而作為藝術(shù)共創(chuàng)團(tuán)體的集體性創(chuàng)作,“自然時(shí)刻”的展覽場域從之前的綜合體驗(yàn)空間,到此次的美術(shù)館,其不僅指向了現(xiàn)有藝術(shù)體制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單調(diào)的現(xiàn)象趣味,更試圖從形式構(gòu)成上宣告創(chuàng)作者被重新分配的話語權(quán)。 位于美術(shù)館二層挑空圓形空間的裝置作品《72》。
《72》是此次展覽的第一件作品,也是整個(gè)展覽敘事語境的基調(diào)。視覺感觀上輕盈唯美,仿似懸浮的“蒲公英”(或者用藝術(shù)家的描述:“蔥花”)一般的裝置,細(xì)看卻是由抗原試劑棉簽制作而成。每72支棉簽構(gòu)成一朵“花”的同時(shí),也隱喻著經(jīng)歷一次72小時(shí)的核酸試檢。這個(gè)數(shù)字,代表著人體病激反應(yīng)的適應(yīng)維度,也是過去三年的生活場景里,全人類群體經(jīng)驗(yàn)的一個(gè)象征性錨點(diǎn)。
于是,通過一個(gè)象征意味的數(shù)字和具有特定文化屬性及事件話題性的材質(zhì)“試劑棉簽”,以詩性的藝術(shù)手法,重新書寫“抗疫”的經(jīng)驗(yàn)文本,是這件作品最令人驚艷之處。如此沉重,如此輕盈!作品中,生命的轉(zhuǎn)變、消亡和看似平靜的堅(jiān)韌,是一條從屬于“自然”的繁衍與消逝的動(dòng)線,每個(gè)觀者都將在其間找見自己的篇章。
自燈塔空間相連的窄道穿過,進(jìn)入展覽的第二空間的瞬間,滿地枯黃的落葉,在沉重有如機(jī)械律動(dòng)的“呼吸”聲中,體驗(yàn)從視網(wǎng)膜蔓延至全身的感官。觀者會(huì)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中不自覺地沉靜下來,在邁腳踏上落葉的同時(shí),進(jìn)入作品所提供的情境。展廳中央的環(huán)型,乍看猶如露營地的觀景臺(tái),然而圓形的矩陣,在方正而靜謐的美術(shù)館空間中卻顯露著清晰的儀式感,仿佛一方位于叢林深處祭奠的云壇,迫使觀者摒棄旁余的肖想,聚焦于當(dāng)下遍地枯槁的深思,抑或情緒的內(nèi)觀。
作品的名字是《樹說》,顧名思義是“樹的述說”。只是當(dāng)作品發(fā)生的現(xiàn)場不是位于郊外森林,而是在作為知識生產(chǎn)的美術(shù)館公共空間中時(shí),情境便只剩表象。于是,“樹”訴說了什么?是周而復(fù)始的生命流轉(zhuǎn),還是自然生機(jī)在后科技時(shí)代所締造的末世焦慮中情緒的缺失?抑或是,當(dāng)生態(tài)視覺的發(fā)生地不是近郊而是美術(shù)館時(shí),被困在系統(tǒng)之內(nèi)的究竟是它們,還是我們?
展廳中,與《樹說》對應(yīng)掛著的是史健的油畫《森林-系列4》,畫作在某種程度上延伸了《樹說》的創(chuàng)作意境,但以一件情境體驗(yàn)裝置而言,《森林-系列4》更像是一個(gè)情感歸逝的出口,承載著呼吸的留白和閑適的遐想。
自一旁的樓梯抵達(dá)美術(shù)館四樓的展廳時(shí),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作品《聽ting停》。沉靜幽暗的畫面中,一息白練直穿天際,耳邊隨即聽到了潺潺的流水聲。走近才知,這是一件聲畫創(chuàng)作,由史健的畫作《夜曲》與聲音藝術(shù)家徐斯韡收集的白噪音構(gòu)成,試圖在聽覺的觸感中,延伸繪畫的意境。用這件作品關(guān)聯(lián)《樹說》和四層空間的展覽敘事,實(shí)現(xiàn)策展線索的轉(zhuǎn)承啟和的同時(shí),在和煦的情緒感知中,將觀者帶入“科技與自然”視角——四樓展廳的第一部分闡述里,作品《竹林七賢03:00:31》和《樹shu術(shù)》都是從科技化與后工業(yè)的角度,對自然景觀的凝視。
《竹林七賢03:00:31》是數(shù)字藝術(shù)與聲音藝術(shù)的合作,[nature moment自然時(shí)刻]團(tuán)隊(duì)將徐斯韡收錄的安吉竹林里的雷雨、溪流、昆蟲、動(dòng)物、竹林、風(fēng)等聲音,通過計(jì)算機(jī)編程轉(zhuǎn)化成以計(jì)算機(jī)特有符號為元素的圖像,以此解析的“自然景觀”,在某種程度上,是精確的數(shù)據(jù)處理機(jī)制對于自然認(rèn)知的審美性的補(bǔ)充。值得一問的,感知的經(jīng)驗(yàn)與數(shù)據(jù)化可視的抽象圖案之間如何筑就通感的對稱?以此對應(yīng)近兩年話題性極高的Ai創(chuàng)作,以及資本關(guān)于Ai智能化社會(huì)的藍(lán)圖構(gòu)想來看,這似乎是個(gè)矛盾,但或者也正預(yù)示著創(chuàng)作者態(tài)度的曖昧——科技可以促成認(rèn)知維度的清晰和冷澈,亦或成為認(rèn)知的障礙。
與之相對的,《樹shu術(shù)》更像是以數(shù)字化的方式,嘗試用工藝和行為重構(gòu)自然和文明的關(guān)系,即便這件作品最初是基于材質(zhì)的探索。36500根木條在經(jīng)過精密的計(jì)算、切割、手工拼接和上色后,以史健的畫作《群山-系列1》為原型創(chuàng)作的《樹shu術(shù)》,正如作品介紹所言,其背后隱匿了技術(shù)、時(shí)間和共同協(xié)作的關(guān)系美學(xué)。除此之外,作為自然生長機(jī)制之一的樹,從原初的植物到成為建筑或工藝制造的基礎(chǔ)材料,再到最終被以另一種非自然的方式鐫刻成時(shí)間,其中關(guān)于技術(shù)文明演變的敘述不言而喻。
穿過四樓展覽的第一部分,一個(gè)半截層的空間中,展示的若干幅繪畫,以及裝置作品《嶺ling靈》和《卵luan亂》,是關(guān)于“自然時(shí)刻”第一次展覽的“回顧”,也是主創(chuàng)團(tuán)隊(duì)希望以“自然時(shí)刻”作為創(chuàng)作主旨,在不同的語境中,持續(xù)不斷梳理和探討生命、社會(huì)和生態(tài)關(guān)系的理念及初心。但在策展的文本中,更像是在片段式的闡述之后,經(jīng)由一段簡介的描述,重新將觀者的注意力拉回對于“自然景觀”的審美探討。在展覽的最后兩部分里,不論是史健的繪畫,還是一乙的景觀攝影,都分別自主觀與客觀的角度,對“景觀”提供了自己的觀點(diǎn)及判斷。
相較于史健以細(xì)膩筆觸對“自然景觀”的情緒塑造,一乙的《瞰》系列,卻在聚合方寸之中,用攝影記錄的方式,在自然景觀與人造景觀之間,延展了美學(xué)關(guān)系的體驗(yàn)。乍看之下猶如抽象構(gòu)成的畫面,實(shí)際是一乙使用無人機(jī)航拍的人工作物景觀,卻以一種天然唯美的狀態(tài),打破自然景致與人造景觀之間矛盾關(guān)系的同時(shí),提示了人工造業(yè)對人類生存生態(tài)的影響——景觀自然,而生命活動(dòng)的軌跡是另一種審美經(jīng)驗(yàn)的缺失。
展廳最后一個(gè)空間,有些特別——史健的動(dòng)物系列畫作和李丹的作品《神經(jīng)元》形成了有趣的敘事:灰褐色的畫面中,圈困于咫尺之間的野獸,悲憤壓抑著執(zhí)拗掙扎,在沉壑之下努力爭取呼吸的一席之地;
與之對應(yīng)的,由若干紅磚塊堆疊的裝置《神經(jīng)元》,仿佛廣廈傾頹的斷壁殘?jiān)`之下是一座建筑或者一方城市曾經(jīng)的鮮活和破敗的記憶。而縱是如此,被時(shí)間鐫刻的文明和生機(jī),在人類不斷迭代的技術(shù)革命與歷史的重建中,不斷翻新流轉(zhuǎn)。此刻,“磚”與“樹”一樣,不僅是材質(zhì)或者建筑元素,其指向了人類歷史所構(gòu)筑的生態(tài)文明的形態(tài)。作品中那些透明的3D打印磚塊,看似以一種兼容重組的姿態(tài)構(gòu)建了城市建筑的新的歷史,但同時(shí)也在提示著,人造景觀對于人類長久的回望。
《神經(jīng)元》讓人忍不住想起俄羅斯藝術(shù)家伊麗薩維塔·科諾瓦洛娃(Elizaveta Konovalova)的《舊城》。同樣是以“磚塊”作為語言,伊麗薩維塔則是用自己徒手收集而來的25,000塊磚塊殘片,回溯了德國漢堡市在二戰(zhàn)硝煙中被摧毀的記憶,以及在時(shí)間的長河里逐漸被沖刷的歷史。以此聯(lián)系到當(dāng)前的國際環(huán)境下頗為尷尬的“俄烏戰(zhàn)爭”,“紅磚”筑起的所謂文明在流離失所面前可笑而無知,那些被封存和鐫刻的真相在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之后,是將被新的建筑技術(shù)方式清洗或是呈現(xiàn)?答案不言自明。
展覽的最后一件作品《褥ru入》同樣也是“自然時(shí)刻”第一次展覽時(shí)即展出的作品,共藝團(tuán)隊(duì)以藝術(shù)家史健的繪畫作品《疏影-暗香》為基礎(chǔ),將畫布材質(zhì)替換成高彈紡織棉,用以模擬“躺進(jìn)”自然中溫暖愜意的感受。為使感受更加直觀,主創(chuàng)團(tuán)隊(duì)更是以觸發(fā)式吹風(fēng)與聲音裝置,強(qiáng)化觀者躺入畫中感受“自然”的體驗(yàn)。“褥”和“入”諧音,前者提示了材質(zhì)和關(guān)系,后者強(qiáng)調(diào)了行為——進(jìn)入如被褥環(huán)抱般舒適的“畫面”,體會(huì)遠(yuǎn)離喧鬧“躺進(jìn)”自然的閑適與溫暖。盡管概念如此美好,卻依然忍不住叫人疑惑:當(dāng)寓意著后現(xiàn)代工業(yè)機(jī)制的紡織面料和試圖抽離環(huán)境束縛的畫作形成對應(yīng)時(shí),這種矛盾的并置,似乎也預(yù)示著當(dāng)科技制造被作為欲望機(jī)制重新度量,那么隨之而生的關(guān)于生產(chǎn)和存在的意義,或許能讓我們從當(dāng)下所處時(shí)代避無可避的憂慮中臨時(shí)抽離。
[nature moment自然時(shí)刻]是由情境體驗(yàn)設(shè)計(jì)團(tuán)隊(duì)樂山樂水™發(fā)起的一個(gè)“共藝聯(lián)盟”,主創(chuàng)團(tuán)隊(duì)希望通過這個(gè)聯(lián)盟關(guān)聯(lián)不同領(lǐng)域的創(chuàng)作者,以“自然”作為協(xié)作的切入點(diǎn),在早已固化了機(jī)制生產(chǎn)的藝術(shù)系統(tǒng)中呈現(xiàn)另一種協(xié)作式的觀念生產(chǎn)和藝術(shù)創(chuàng)建機(jī)制。但事實(shí)上,不管是1909年在德國慕尼黑成立的“藍(lán)騎士”(The Blue Rider),進(jìn)入后現(xiàn)代主義語境后出現(xiàn)的藝術(shù)家組合,如吉爾伯特&喬治,艾默格林&德拉賽特,或者藝術(shù)團(tuán)體Raqs媒體小組、“六島”(island6),其初衷和工作模式實(shí)際都是在對著作者的權(quán)利格局與表達(dá)的協(xié)作機(jī)制提出質(zhì)疑和觀點(diǎn)。
因此,如何看待[nature moment自然時(shí)刻]這個(gè)共藝聯(lián)盟,就像約瑟夫·博伊斯(Joseph Beuys)生前的最后一件創(chuàng)作《卡普里電池》——由一只酸檸檬和一枚燈泡組成,檸檬為燈泡提供能量——所示:在一個(gè)發(fā)展迅捷的想象力枯竭的高質(zhì)化社會(huì),或者只有這只“酸檸檬”,才能夠在意想不到的時(shí)候獲得重啟的能量。對于聯(lián)盟發(fā)起者樂山樂水™來說,[nature moment自然時(shí)刻]或許就是這只“酸檸檬”,其首先解決的,不是照亮誰,而是為“燈泡”提供能量。 作者/展覽評論人:Nikita Yu
資深藝術(shù)工作&寫作者。安大略設(shè)計(jì)藝術(shù)學(xué)院批評與策展專業(yè)及復(fù)旦大學(xué)心理學(xué)專業(yè)研究生。自2014年起從事藝術(shù)寫作、評論及策展等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,為《Nowness》《Hi藝術(shù)》《Connaissance des Arts》《芭莎藝術(shù)》《美術(shù)文獻(xiàn)》《ZAIART》等媒體撰稿人。 |